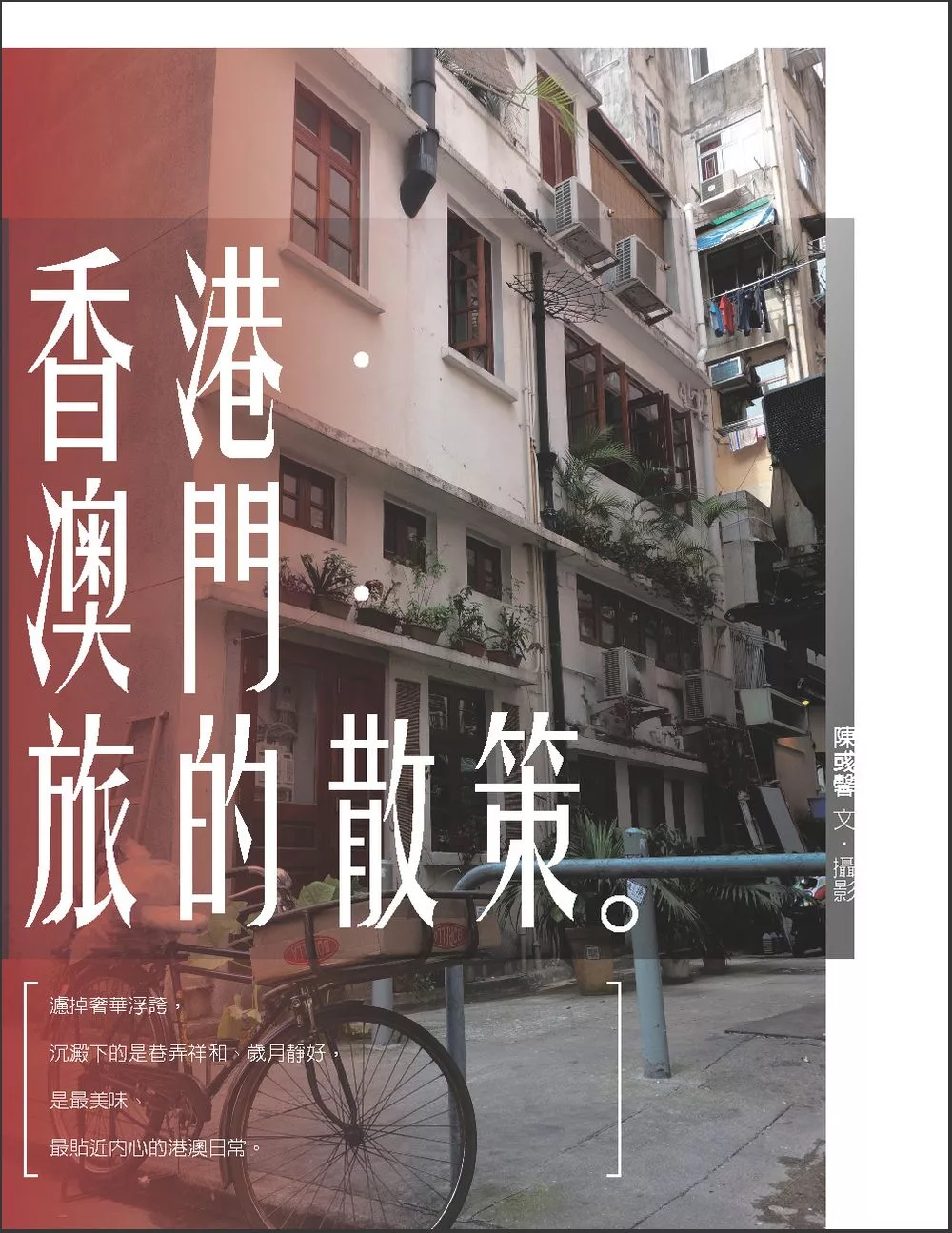Copyright © Jas Chen
「這麼喜歡紐約嗎?」同事在午休時分經過小小的辦公室,探頭對著正在一張張檢視紐約照片的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喜歡紐約嗎?
如果說,把對於紐約許多複雜難辨的不同情感綜合起來看,那麼裡頭應該是包含著「喜歡」這樣的情感在內。不過「喜歡紐約嗎?」對於這樣的問題,似乎總難爽朗地直接大聲地說是。這樣說吧,如果喜歡路上行人漠然沒有笑容的臉;喜歡以每個街口或尿臊、或腐爛水果甜氣、或陳年垃圾、或濃重隔夜酒臭味來鍛鍊嗅覺與記憶力;喜歡衝著人大按喇叭的凶狠計程車,或計程車上總有繚繞不去的印度燃香味……那麼必然能成為一個十分喜歡紐約、至少是喜歡曼哈頓的人。
那麼,原來我不喜歡紐約嗎?
是喜歡的。喜歡隨意就可以翻找到二手古董的小店和露天市場;也喜歡各色不同的大都會、古根漢、摩瑪、自然歷史博物館;喜歡學著觀光客坐上白色的馬車,指定繞行時報廣場以便享受車水馬龍間的30年代;喜歡公園大道上一棟棟高級公寓門口立著、戴著大圓盤帽、繫著領結,西裝筆挺的門房;有時只是喜歡一早起來可以馬上下樓買一個結結實實的猶太麵包做早餐,然後配上淡淡的咖啡在陽光下閱讀週日版的紐約時報……
在紐約四年,我當然可以再列上各一百條喜歡與不喜歡的理由,然而這些說的出來的好處,許許多多其他美麗悠哉的城市也都擁有,甚至更美麗悠哉一些。那麼,已然拜訪過那些更美麗的城市的我,為什麼對於紐約如此念念不忘?
「因為你中毒了。」從來沒踏上美國的同事不以為然地回座位去解決他吃了一半的午餐,如此這般地結束我的難題。
「因為你中毒了。」能夠這樣解釋說不定也很好?我想。於是將廣東粥配滷味的午餐繼續擱置一旁,無法停手地整理紐約照片。不過,中什麼毒呢?
是一種叫做「全然的自由」的新種毒藥吧。
在這個複雜的城市,不論多麼怪異的穿著,扮裝皇后、僅穿著馬靴牛仔帽閃亮腰帶與超人內褲的強壯男人、全身上下釘滿了各式鼻環耳環眉環肚臍環的「洞洞人」;多麼怪異的行徑,沿路走路跳舞、藉著人行道作畫、對著無辜路人大肆咆哮…都不足以讓早已習慣光怪陸離紐約客多望上一眼。這可是一個可以在週六拿到週日報紙的地方,沒有什麼能叫人訝異。
在紐約,可以不說話、不照規矩、不打招呼、不微笑,可以只做自己,一個就只是「一個人」的身分。
這就是那種叫做「全然的自由」的毒藥吧。讓我不斷不斷地想回紐約。
攝於紐約˙第六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