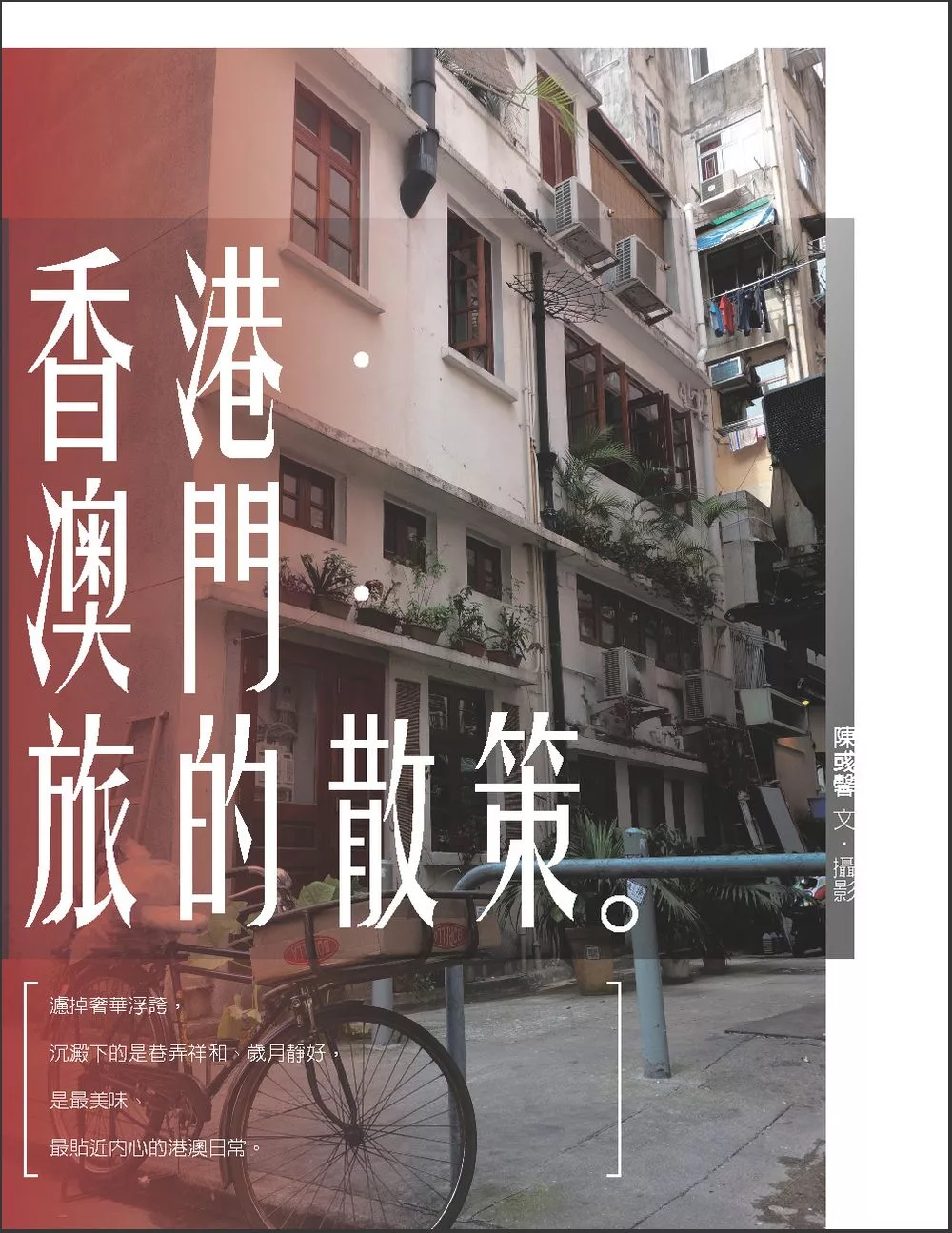Copyright © Jas Chen
「彧馨,你知道找到世敏了嗎?」
「彧馨,來,我給你世敏手機。」
「彧馨,我那天在演唱會碰到世敏了欸!」
從維也納回來,MSN屬於「超級老同學」那一欄裏的「超級老同學」們,以一種瘋狂的速度傳送各式各樣關於「找到董世敏」這個消息。
尋找董世敏,已經是持續一個多月的事情了。
剛開始是因為一場「十年同學會」,非常熱心的同學Helen架設了一個班版,方便老同學貼些新消息。不過,如您所知,會來張貼的人總也是那幾個,保持失聯的人總也繼續保持失聯,這在每個人的人生中都會發生,沒什麼好說的。
彧馨曾經也是短期的「失聯人口」之一,對於被幸運「拾獲」這回事,一直心存感激。不過,所謂物以類聚,彧馨當年的學伴兼室友,也就是本文主角「董世敏」小姐,則一直是長期以來的失聯人口。
我一直想找她,但也一直沒有很強的動力去尋找。當然在同學會也詢問過一些屬於「包打聽」等級的同學,但每個人都是兩手一攤,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彧馨,你有世敏消息嗎?」某日Helen在MSN這樣問我。
原來,世敏的某個堂兄居然找到了班版,透過班版聯絡上Helen,客氣地詢問世敏的消息。
「不會是出了什麼事吧?」Helen和我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
「你去想你曾經有的消息,我也透過一些方法來找找看。」
Helen是記者,事實上我的許多同學都是記者,的確可以透過很多管道找人。
我呢?從前尋找世敏是偶一為之的念頭,現在好像變成念茲在茲的要務。不過,「不應該會很難吧?」我想找不到世敏是因為沒認真找,既然要開始找了,總會找到的吧?
至少,開始時我是這樣想的。然後放心的讓神通廣大的Helen去忙。
「彧馨,我朋友說戶籍地址沒有變,還是那裏。」
「彧馨,通訊錄上的電話變成傳真,我來傳真看看。」
似乎算是有個好的開始。
「彧馨,傳了過去都沒有回應。你還知道其他訊息嗎?」
一個星期遊手好閒,好像也該來略盡一點綿薄之力,我努力思索跟世敏有關的記憶,一面在辜狗大神搜尋欄裏打下「董世敏」三個大字。
什麼都沒有,除了大學榜單。
嗯,我還記得世敏妹妹的名字。繼續辜狗。
還是什麼都沒有,除了八百年前松山高中合唱團指揮資料。(原來世敏妹當過指揮?!)
再努力想想,我還記得世敏媽媽的名字欸!剛巧又是很特別的姓。
繼續辜狗。這次有了,不但找到服務單位,居然還有一筆捐款資料,裡面內容包含身份字號和家裡、手機的號碼。(什麼啊?這真可怕!找到時心裡這樣想。)
順著資料上的號碼打去,一隻是空號,一隻有人接起來了。
「請問是某某某嗎?」「我是瑪麗亞啦。」
「啊?」「我是菲傭菲傭啦!」
一陣兵荒馬亂,電話另一面用英文+台語+國語+菲律賓話說他完全不認識某某某。(應該是這意思吧?)
都什麼年代了,為什麼這一家子都沒有一丁點資料可以在網路上找到呢?(哭)
我努力不懈的打電話到董媽媽工作的單位詢問。
「她好幾年前就退休囉!聽說移民去美國了。」
想起世敏以前常去的一間教會,於是一個餐酒會後,開車去了士林。教會所在地已經記不太清楚,總之是在劍潭站附近的小巷弄裡。在亂七八糟的小巷裡找到應該是的地點,還有十字標記,但似乎空無一人,找了附近的鄰居詢問,說教會已經許久沒有人出入了。
束手無策。而我已經要出發去奧地利了。
找不到了嗎?
沒抱希望,但是「董世敏尋人任務」卻已經悄悄在準備奧地利的行程中圓滿達成。
「我直接去她家碰運氣,沒想到她媽媽剛好也從美國回來,就這麼聯絡上了。」
在三人同聚的超迷你同學會上Helen這樣說。好不容易被找到的世敏則是基哩瓜拉分享大堆亟需被update的資料。
不管怎麼樣,尋人任務總算圓滿達成。
我們找到了同學。
堂兄找到了堂妹。
世敏當然也找到了他的大學歲月。
特別記上這篇亂七八糟的文章,也特別標記了「董世敏」三個字,這樣以後有人要找擅長失蹤的世敏,應該就不至於這樣困難了吧?
攝於維也納˙一張肩負尋找鋼琴新主人的超級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