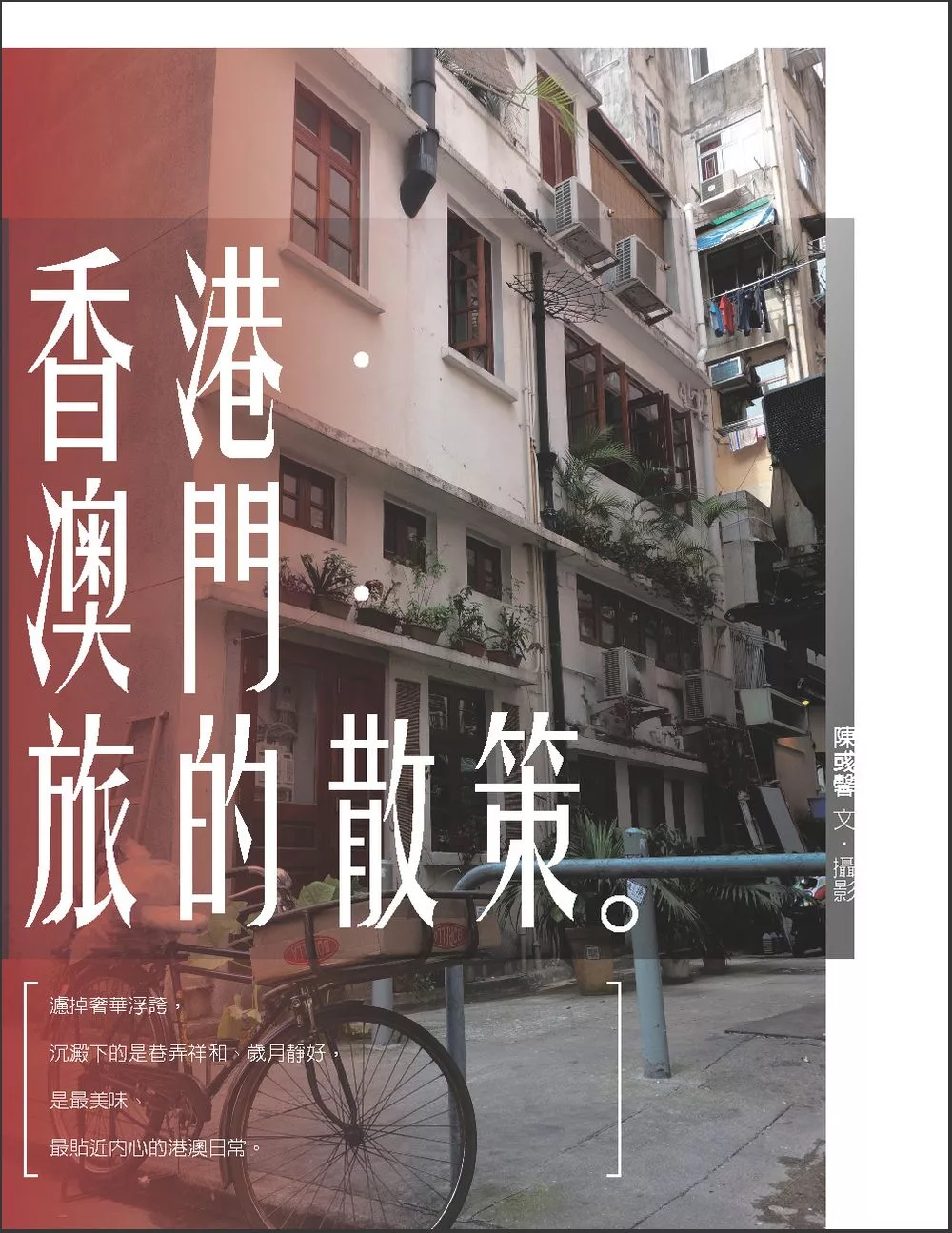原刊載於2009/03/02.UDN
Copyright © Jas Chen
若說巴黎「曾經」有什麼我想去得要命的咖啡館,非加尼葉歌劇院附近的「大咖啡館」(Le Grand Café)莫屬。原因無他,就因為在1895年12月28日這一天,此處是世界上第一部電影放映的地方。光是這一點,就讓研究所念電影的我嚮往非常。
只是晚了一步。
特意在出發前查詢大咖啡館的相關資料,才發現象徵巴黎某個時代咖啡館興盛的大咖啡館在不久前步入生命終期,已然歇業。這簡直不可置信!大咖啡館曾是24小時全天候那樣風光的營業,是什麼原因讓它闔上美麗的章節的呢?看著手中所有的大咖啡館黑白照,有些茫然。至於改裝後的現址,很抱歉地興趣缺缺。雖然現址除了新建的史懷柏飯店(Hotel Scribe Paris),也還有小小的紀念館,但我總偏執地覺得,去看已經再也不是的老地方,除了惋惜,還會多上一丁點對新地方的痛恨。
不過怎麼說,巴黎的咖啡館還是很神奇,連第一部電影都能在此放映,還有什麼是不能在咖啡館發生的呢?
抱著這樣的心情,我走入並不陌生的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
老實說吧,住在巴黎第六區,可以找到的咖啡館只怕有上百家那樣多,實在沒有必要到隨時呈現「爆滿」狀態的花神咖啡來跟觀光客擠。然而,正坐落在聖捷曼大道上的花神,除了擁有大片落地窗、與對面的利普啤酒館(Brasserie Lipp)、隔鄰的雙叟咖啡館(Les Deux Magots)同享盛名之外,似乎還多了一點什麼。
有晚娘臉孔和脾氣的收帳婦人?傲慢的領班?來自日本的侍者?年輕得不像話的新任經理?還是一張張以花神咖啡館為主題的老照片?
我其實不知道。
落雪的巴黎早晨,我一如以往地進入花神,一如以往地落座在猶如溫室玻璃屋般面街的座位,雖然不過八點半,要找到一張座位也並不是那樣容易。冬日是咖啡館的旺季,除了觀光客,如鄰桌那樣同領班來四個頰吻的巴黎熟客也滿滿都是。
兩個日本女人在大清早上了濃妝坐在咖啡桌前吃著可頌,輕聲說著話,也當心不讓麵包屑掉在花色鮮艷的領巾上。年輕的學生旅客節省地喝著牛奶咖啡,亮閃閃的眼睛羨慕的盯著別桌客人面前豪華的花神早餐。看似巴黎熟客的優雅女士不知道為了什麼一連叫了六個水煮熟雞蛋,美麗的裝蛋器一排排立在桌上,上面的蛋一點沒動,女士卻要結帳了。某個花神侍者拿起托盤好擋住落個沒完的雪,急匆匆地從正門走出,隔壁雙叟的侍者剛好出來抽菸透口氣,見著彼此喊了幾聲算做招呼,便又各做各的事…我一面吃著剛端上來的蛋捲早餐,一面靜靜地將左右的事物收進眼底。
昨晚讓我拍照的侍者從桌邊走過,彷彿認出我似地朝我眨眨眼。
巴黎的咖啡館是這樣的,如果熟悉了某家的氛圍,那麼坐進了咖啡館,便似乎能感受段段不同的故事以不同的語言同步進行著,彷彿多軌電影,我便如同坐進貴賓席的電影觀眾,得以一邊享用熱呼呼的咖啡一邊觀賞齣齣不同的劇碼。
正想著,窗外卻有人拿起相機將花神咖啡的招牌及招牌下的我一同攝下。
喔,也許有時,觀眾會變成主角也說不一定。
 Copyright © Jas Chen
Copyright © Jas Chen














 心儀
心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