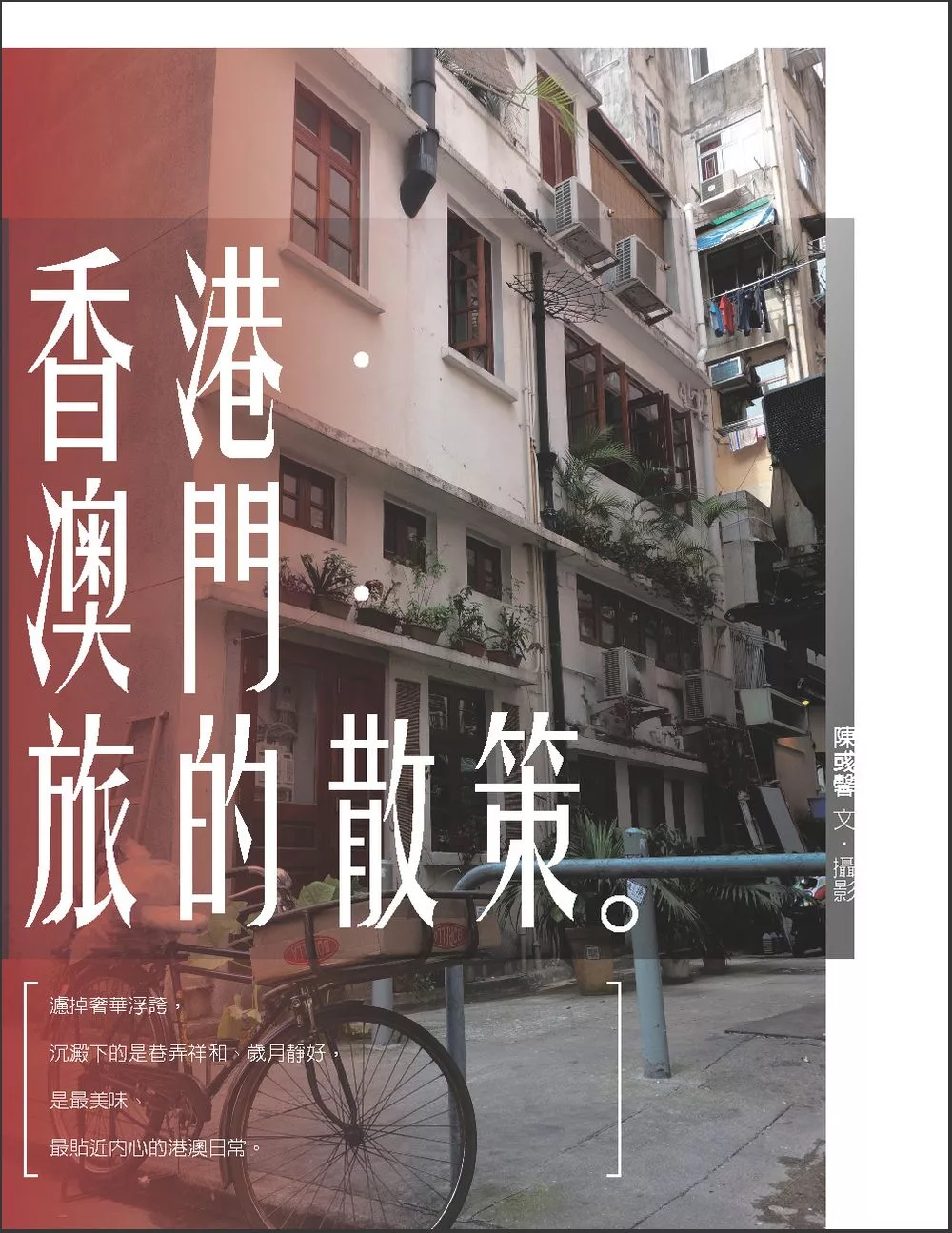© Photo by Jas Chen
無論如何都想去旅行。近來時時有著這樣的想法,但生活中仍有許多的放不下,所以,時時地在網路中悠游著尋找明知道不怎麼可能使用的廉價機票與行程,以稍稍抑止胸口的疼痛。
London & Paris Sale
From $799Book by June 18th
Experience both London and Paris for one low price!
Packages Include:Roundtrip air on available carrier
4 night hotel accomodations in each city
One-way rail transfer from London to Paris
Continental breakfast daily
看到這樣的行程,忍不住懷念起居遊在倫敦的炎夏,與在巴黎的春末和初秋。
無意間發現曾經待過的巴黎老飯店是被人這樣評價的:
Mercure Ronceray-Paris Opera Hotel
We up graded our hotel in Paris to Mercure Ronceray. No shower just a bathtub that is so narrow you have to stand sideways. When we walked it the room there was one light with a 25 watt bulb. We could hear the people next to us partying all night. The front desk people were very rude. I had bought an adapter for the electrical and it did not work in the room. When I asked at the front desk they said they don't work in any of the rooms because the electrical was too old. I was very upset they didn't even have a blow-dryer. Oh one more thing no coffee machine in the room and there breakfast sucked. When we where ready to checkout to catch our train to Rome they couldn't find our luggage. We nearly missed the train it was very stressful. Won't go back there again.
我忍不住莞爾一笑,巴黎的飯店的確是窄小老舊又不便,麻煩的電器設施、時時沒有熱水,且廁所真是小到不知道如何好好地把臀部安放在馬桶上那樣地糟糕。然而我還記得,住在此間時,可以推開長窗,深深地吸入屬於花都的氣息,帶著一點街角販售奶蛋薄餅的香味,和下方麵包店剛出爐棍子麵包的熱氣;也記得三三兩兩的人群,無所事事地漫步在鵝卵石鋪成的古老街道上,剛下過雨,石子地晶亮,而白牆與墨黑的雕花鐵欄杆則襯得更加清楚。
「欸,無論如何都非常地想旅行啊!」我這樣地對自己訴說著。
對了,怎麼會有人想在巴黎喝機器咖啡呢?
攝於坎城‧一個不在巴黎也不在倫敦、然而常有這兩地名人來居住的卡爾頓飯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