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Photo by Jas Chen
一早就知道不是個好日子。
很少睡得好,尤其最近,思緒複雜,雖然不能說時時睜著眼睛等天明,不過輾轉難眠是常常發生的。即使與友人相聚的時間似乎變多、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可以讓人愉快的事也日漸豐富,可是一個人窩在房間時,「我是誰?為什麼我在這裡?人為什麼要睡覺?」這樣亂七八糟、如出一轍的問題,總是嗡嗡嗡地作響。村上春樹在某本書裡提到,他的腦子裡似乎住著兩隻蜜蜂,時時吵得不得了。不知道是不是那隻叫做卡卡的蜜蜂在村上的腦子裡住煩了,款款包袱跑到我的腦子裡度假也說不定。總之,難以入睡的我,對著鏡中兩隻黑到了眼眶下的眼睛很是煩惱。
伸手拿起據說可以美白的雪肌精,窄小的檀木螺鈿櫃琳琅滿目的放著瓶瓶罐罐,十分擁擠。我總是當心地拿,從來沒有碰掉過任何物品。一如平常地旋開化妝水瓶蓋,檀木櫃上,好友送我的白瓷圓盒好端端地突然落了下來,漂亮地彈跳在旁邊矮了一截的除濕機,再彈落到柚木地板上。盒子上印製的精緻貓圖案裂成兩半,七八隻三色的、虎斑的、黑白的花貓咪慵懶地在木質地板上滾動著,揮手跟已然呆掉的我打招呼。「可沒有碰到盒子啊?」心裡這樣嘟囔著,隱約有些不怎麼對勁的感覺。
下樓查看撿回來的幼鳥。
家裡住在山邊,前後院都是高高的樹木,小池子裡有蛙鳴蟲叫,偶爾的夏夜,還能看到幾隻螢火蟲。這樣的環境鳥是不會缺席的,然而築巢總是不夠大的樣子,每年繁殖期,都會有幾隻幼鳥掉出巢外。雖說總是帶回家小心地保溫、餵食煮熟的蛋黃或泡過水的飼料,但多半是羽絨也沒長全的小傢伙,有些已經有著明顯外傷。掉出巢的那一剎那幾乎就宣判了死刑。既然餵養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撐不了很久而不得不在後院子埋鳥屍時,也就不會這麼悲哀。怎麼說,都不會比在硬石板地上等死來得差吧?我總是這樣安慰自己。
這一次的小鳥相當的大呢!擱在白文的籠子裡,白文成鳥彷彿成了幼弱的那一隻。雖然說羽翼仍不能算豐全,但怎麼看,存活的贏面總要大一點。我照舊搬出大小不同的針筒,準備飼料灌食。野鳥是不會乖乖吃飯的,雖然有些粗魯,但不撬開鳥喙是不行的唷!於此我已經很有經驗,三兩下可以就手。這一次的幼鳥嘴喙部分並不平整,曲曲折折,很怪的樣子,不知道是隻什麼鳥?門前的樹很高,我是見不著鳥巢的,也不見親鳥找尋。
「不過,」我想著「也許只需要再養幾天就可以放飛?」
餵食完畢,準備放下鳥兒。可非常突然的,原本相當頑健硬朗的鳥兒突然地倒下。本來挺得直直的頸項,像是紐約世貿中心一般,突然地軟了,塌陷下來。
一秒前還很有生命力的與我爭奪著,後一秒脖子就整個地軟掉了。小鳥的眼睛閉上,身體仍然溫熱,是原本以為再兩天就可以放飛的生命……「是餵了不該餵的東西嗎?是餵得太多嗆著了嗎?是我太用力了嗎?」到底是哪裡做錯了呢?我不斷地問自己,始終沒有辦法很輕鬆地看待。雖然來來去去送走了一些生物,可是從來沒有眼睜睜地看見生命在指尖之中流逝,彈指間。
夜裡從機場回家,收音機裡傳來更令人扼脕的消息。風光明媚的陽明山,不幸地成為許多人的葬魂之處。回到房間,「啪!」地一聲旋開了收音機,繼續收聽著廣播,聽著從前的長官針對這次事件的發言。我舉起還沒有黏合上的白瓷圓盒,對著燈光看。盒子還可以黏回去,只不過會有幾個缺口,有道裂痕。
今日之中的其它呢?
攝於台北‧自宅
一早就知道不是個好日子。
很少睡得好,尤其最近,思緒複雜,雖然不能說時時睜著眼睛等天明,不過輾轉難眠是常常發生的。即使與友人相聚的時間似乎變多、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可以讓人愉快的事也日漸豐富,可是一個人窩在房間時,「我是誰?為什麼我在這裡?人為什麼要睡覺?」這樣亂七八糟、如出一轍的問題,總是嗡嗡嗡地作響。村上春樹在某本書裡提到,他的腦子裡似乎住著兩隻蜜蜂,時時吵得不得了。不知道是不是那隻叫做卡卡的蜜蜂在村上的腦子裡住煩了,款款包袱跑到我的腦子裡度假也說不定。總之,難以入睡的我,對著鏡中兩隻黑到了眼眶下的眼睛很是煩惱。
伸手拿起據說可以美白的雪肌精,窄小的檀木螺鈿櫃琳琅滿目的放著瓶瓶罐罐,十分擁擠。我總是當心地拿,從來沒有碰掉過任何物品。一如平常地旋開化妝水瓶蓋,檀木櫃上,好友送我的白瓷圓盒好端端地突然落了下來,漂亮地彈跳在旁邊矮了一截的除濕機,再彈落到柚木地板上。盒子上印製的精緻貓圖案裂成兩半,七八隻三色的、虎斑的、黑白的花貓咪慵懶地在木質地板上滾動著,揮手跟已然呆掉的我打招呼。「可沒有碰到盒子啊?」心裡這樣嘟囔著,隱約有些不怎麼對勁的感覺。
下樓查看撿回來的幼鳥。
家裡住在山邊,前後院都是高高的樹木,小池子裡有蛙鳴蟲叫,偶爾的夏夜,還能看到幾隻螢火蟲。這樣的環境鳥是不會缺席的,然而築巢總是不夠大的樣子,每年繁殖期,都會有幾隻幼鳥掉出巢外。雖說總是帶回家小心地保溫、餵食煮熟的蛋黃或泡過水的飼料,但多半是羽絨也沒長全的小傢伙,有些已經有著明顯外傷。掉出巢的那一剎那幾乎就宣判了死刑。既然餵養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撐不了很久而不得不在後院子埋鳥屍時,也就不會這麼悲哀。怎麼說,都不會比在硬石板地上等死來得差吧?我總是這樣安慰自己。
這一次的小鳥相當的大呢!擱在白文的籠子裡,白文成鳥彷彿成了幼弱的那一隻。雖然說羽翼仍不能算豐全,但怎麼看,存活的贏面總要大一點。我照舊搬出大小不同的針筒,準備飼料灌食。野鳥是不會乖乖吃飯的,雖然有些粗魯,但不撬開鳥喙是不行的唷!於此我已經很有經驗,三兩下可以就手。這一次的幼鳥嘴喙部分並不平整,曲曲折折,很怪的樣子,不知道是隻什麼鳥?門前的樹很高,我是見不著鳥巢的,也不見親鳥找尋。
「不過,」我想著「也許只需要再養幾天就可以放飛?」
餵食完畢,準備放下鳥兒。可非常突然的,原本相當頑健硬朗的鳥兒突然地倒下。本來挺得直直的頸項,像是紐約世貿中心一般,突然地軟了,塌陷下來。
一秒前還很有生命力的與我爭奪著,後一秒脖子就整個地軟掉了。小鳥的眼睛閉上,身體仍然溫熱,是原本以為再兩天就可以放飛的生命……「是餵了不該餵的東西嗎?是餵得太多嗆著了嗎?是我太用力了嗎?」到底是哪裡做錯了呢?我不斷地問自己,始終沒有辦法很輕鬆地看待。雖然來來去去送走了一些生物,可是從來沒有眼睜睜地看見生命在指尖之中流逝,彈指間。
夜裡從機場回家,收音機裡傳來更令人扼脕的消息。風光明媚的陽明山,不幸地成為許多人的葬魂之處。回到房間,「啪!」地一聲旋開了收音機,繼續收聽著廣播,聽著從前的長官針對這次事件的發言。我舉起還沒有黏合上的白瓷圓盒,對著燈光看。盒子還可以黏回去,只不過會有幾個缺口,有道裂痕。
今日之中的其它呢?
攝於台北‧自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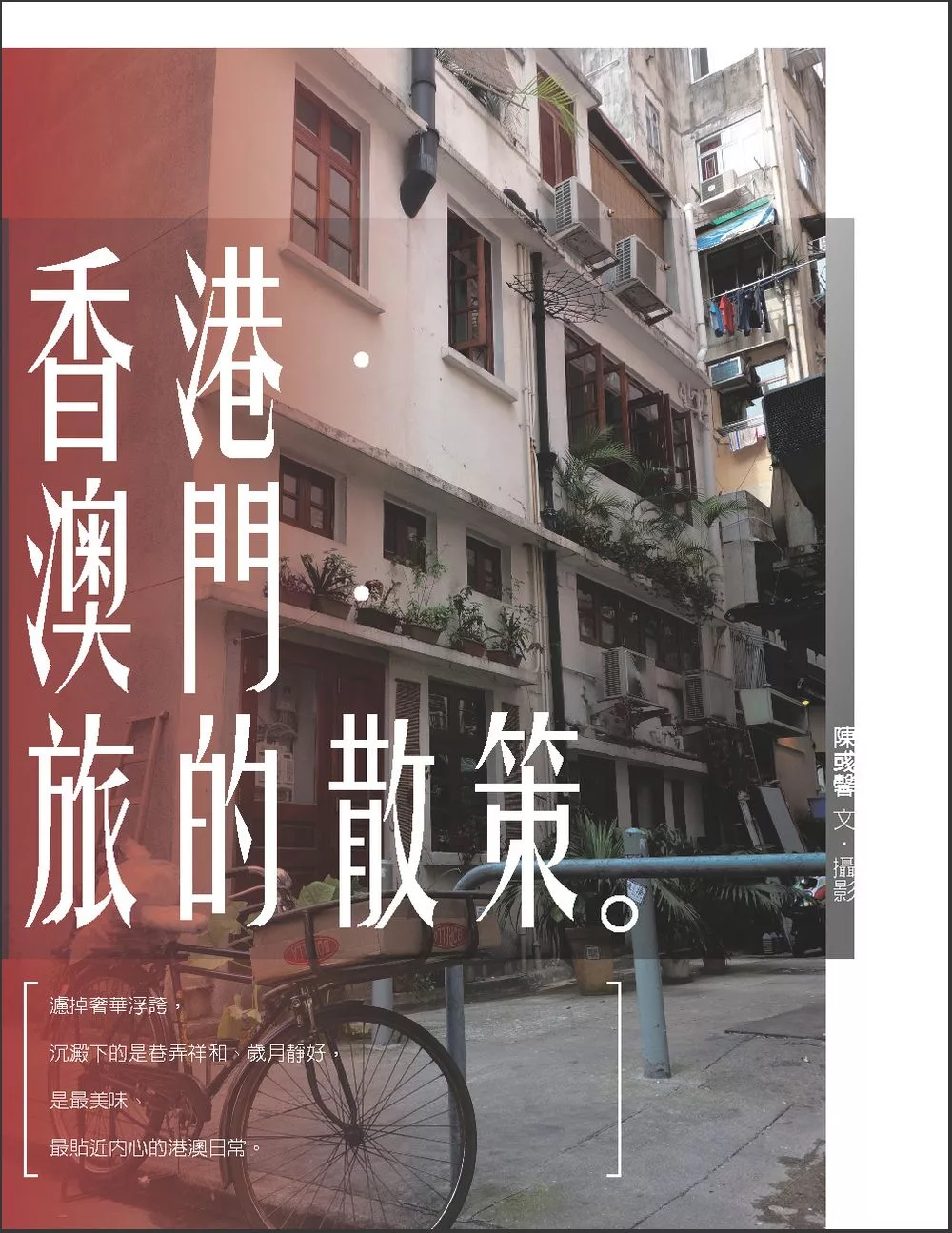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