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氣持續的陰沉,鼻子過敏的老毛病又犯了,成天地擤,鼻翼因而些許泛紅,就要破皮了。不知道為了什麼,關於陰天,我總認為最恰當的,是張愛玲在「留情」裡寫得:「米先生回到客室裏,立在書桌前面,高高一疊子紫檀面的碑帖,他把它齊了一齊,青玉印色盒子,冰紋筆筒,水盂,鑰匙子,碰上去都是冷的;陰天,更顯得家裏的窗明几淨。」這麼一段話。陰天,該是乾淨而清冷的。
台北的陰天多是悶熱,汗珠子會順著毛細孔粒粒冒出來,然後在肌膚與衣料之間流下道道小瀑布,沾連在一塊,不舒服的潮濕。從來也不曾喜歡這種感覺,但這卻是生成在腦海中,有關「家」的記憶。於是在同樣悶熱的夏威夷、波多黎各和坎恩絲,我總忍不住想起台北,潮濕的家,而仍然是家。
也許,有一點不怎麼舒適的記憶,對於故鄉的依戀會更為緊密。某個上班日的午後,我踱著步在忠孝東路二段的烏煙瘴氣之間走著,天陰著,準備下雨,而我仰著臉、迎著灰暗的水氣,真正地覺得回家了。
台北的陰天多是悶熱,汗珠子會順著毛細孔粒粒冒出來,然後在肌膚與衣料之間流下道道小瀑布,沾連在一塊,不舒服的潮濕。從來也不曾喜歡這種感覺,但這卻是生成在腦海中,有關「家」的記憶。於是在同樣悶熱的夏威夷、波多黎各和坎恩絲,我總忍不住想起台北,潮濕的家,而仍然是家。
也許,有一點不怎麼舒適的記憶,對於故鄉的依戀會更為緊密。某個上班日的午後,我踱著步在忠孝東路二段的烏煙瘴氣之間走著,天陰著,準備下雨,而我仰著臉、迎著灰暗的水氣,真正地覺得回家了。
攝於夏威夷‧歐胡島© Photo by Jas 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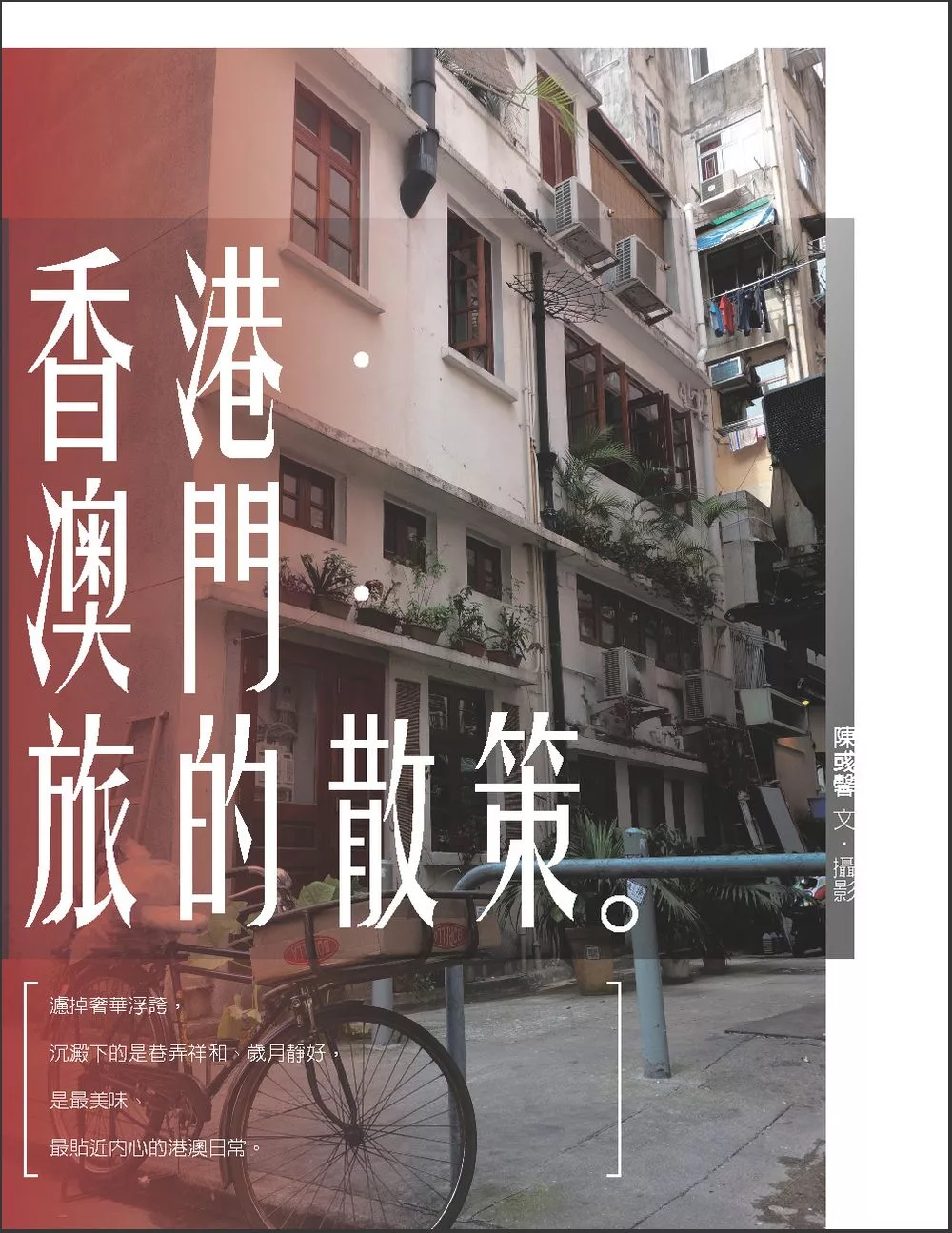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