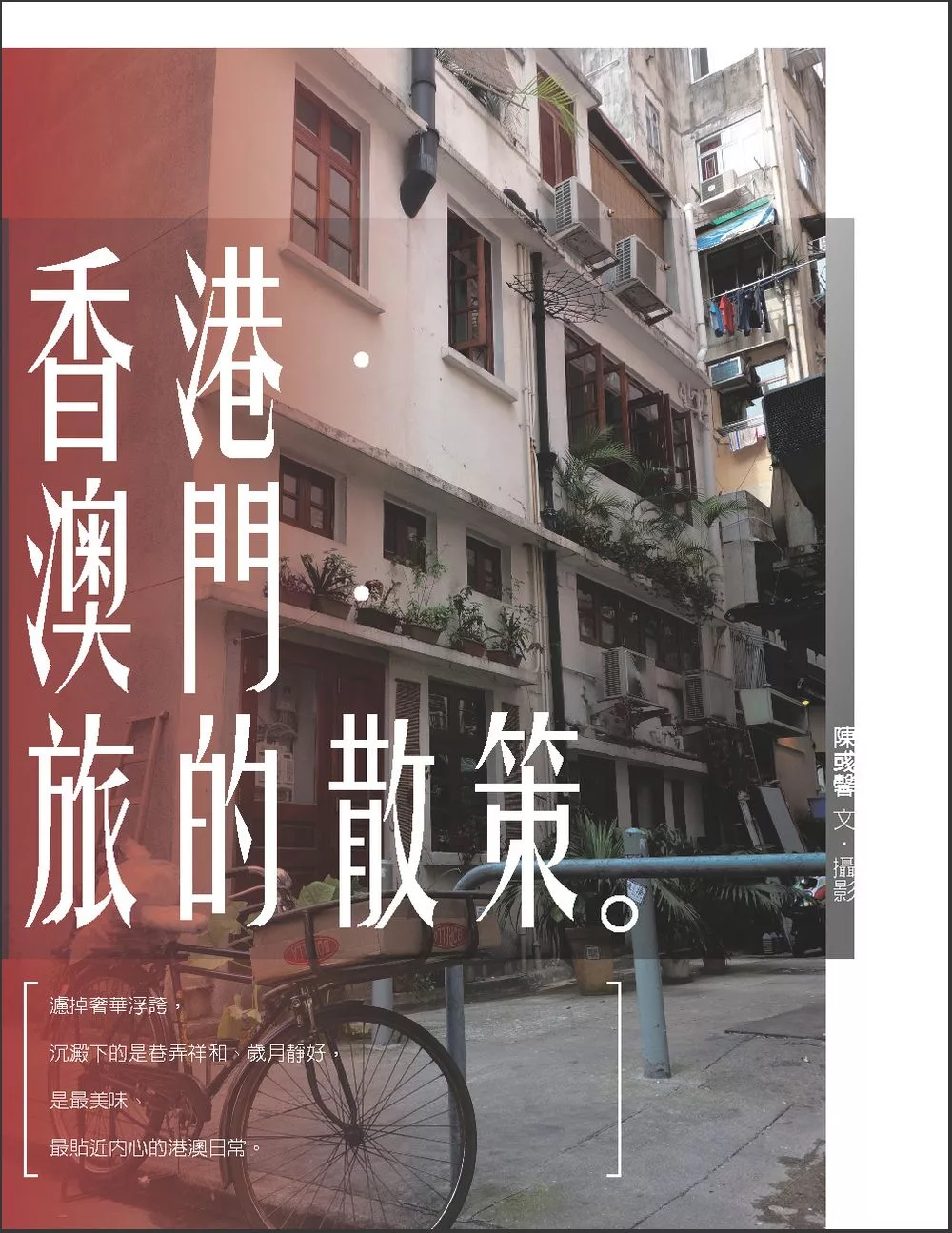(原刊載於02.12.09.UDN)
Copyright © Jas Chen
該走窄小的而充滿藝術風格的小巷,還是該沿著塞納河從新橋走到藝術橋轉彎走進我的巴黎公寓呢?
即將前往巴黎前,將房子租給我的Naomi女士親切地給了清楚指示,方便我找到公寓。她在信上說:如果你從戴高樂機場前來,那麼離公寓最近的地鐵站是奧德翁,走路不過五分鐘,如果乘坐計程車當然方便,不過如果可以,搭RER市郊列車到拉丁區的聖米歇爾站下車是最好的選擇。從聖米歇爾廣場走到公寓最近的道路是聖安德藝術街,雖然是有風味的老街,卻很窄小,如果帶著大件行李就不方便;所以如果提著大行李,也許還是該沿著塞納河一路走到法蘭西學院,穿過法蘭西學院就會抵達公寓所在的Mazarine街了。
不論走哪條路都很棒,她說,你都可以先看到一點美麗的巴黎。
結果…
「真高興聽到你平安抵達巴黎,」大約清晨七點,從戴高樂機場打了電話給Naomi,她在電話裡這樣說,「不過,」電話裡傳來非常為難的聲音,「恐怕妳非搭計程車不可了,巴黎正在罷工中,RER火車和地鐵都停駛。幸虧妳到得早,應該可以避過交通巔峰才是。」
罷工中?來巴黎前剛看了終於出了中文版的《
巴黎,賽啦!》一書,書裏主要說著作者在巴黎一年的生活。其中一部份正是敘述這個美麗城市裡總有數不清的不滿急待抒發,三不五時便要來罷工一番。雖然我自己並不時常來巴黎,但幾次來這個城市都還不曾遇過這個狀況。
「罷工?」所以乍聽到這詞還真是讓我楞了一會兒。
確認了RER和公車完全停擺,好吧,這下不搭計程車都沒辦法了。非常無奈地加入也正抱怨連連的人潮,在排隊等計程車中開始巴黎的第一天。
「嘰哩咕嚕嘰哩咕嚕噗隆於黑...」由於我有坐上飛機即使吃安眠藥也睡不好的毛病,長途飛行後總是累的,心裡打算在車上小睡片刻,眼睛也確實闔上準備假寐一會,可惜為了某種莫名原因,可愛的司機先生開始了碎碎念計畫:「喔拉拉噗離東欸...」老實說我一點都聽不懂司機老先生說的是什麼,除了開頭的「喔拉拉」,不過配合司機誇張的表情及不斷出現的法文發音的巴黎,大概猜出來是要我多看看窗外美麗的景色,到了這裡不該睡覺的意思。
這我也知道嘛,不過老先生,即使是巴黎這樣有名的城市,從機場到市區的高速公路無論如何還是很無聊的,您要我看什麼呢?窗外可怕的車陣嗎?腦筋停了停,等下,車陣?我睜大眼睛看著窗外停滯不前的車輛,再看看跳個沒完的計費表,沒搞錯吧?天不還是黑的嗎,一大清早怎麼就塞車了呢?再想想歐洲冬日天亮得晚,仔細換算了時間,才發現已經是巴黎早上的八點,換言之也就是塞車時段。
天仍然很黑,事實上一直到快九點才算看見曙光。我在一片黑之中勉力打起精神微笑,偶爾點點頭,以便在司機老先生漫長無止境的演說中偶有的停頓間做禮貌性回應。
老先生幾乎沒停過演說,而我總有點錯頭的時候,以至於在擔心跳錶上屢屢增加的花費時還必須應付老先生從照後鏡裡挑眉、蹙眉等等對於我不專心聽講的責怪。車流的速度實在緩慢得可怕,我擔心地看著計費表上的數字,猜測大概坐到巴黎要付出比在巴黎住宿一天還高的代價。看到最後索性不看了,怕價錢高到要心臟病發。
唉,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抵達巴黎呢?
「妳的巴黎新家!」終於,老先生得意地在極其窄小的Mazarine街停下,順便塞住了整條街,一面不耐煩地揮手要想要通過的其他車輛等待,一面優雅地為我搬出行李。
「告訴妳巴黎城市裡不塞車了吧,塞車是城郊那堆工廠的原因。在巴黎要好好玩啊,妳會喜歡這個城市的。」將近一個鐘頭的法語轟炸讓沒有法語程度可言的我多多少少猜到老先生說些什麼,車資也還好沒有想像中貴,最要緊得是天亮了,而我平安抵達小公寓。
隨意收拾好行李,迫不亟待地衝到離小公寓僅有咫尺之遙的塞納河畔漫步,舉起相機在藝術橋上對著法蘭西學院左右拍攝。我心想雖然巴黎行還真像是「賽啦」的開始,不過是在巴黎哪!一切總會越來越好的,不是嗎?
PS.雖然早就離開巴黎,但回想旅程剛開始驚險的第一天,記憶仍然簇新。離開維也納時氣溫穩定回暖,天光初露的時間也日益提早,此時的巴黎不知如何?
一面這樣對抗時差想著,一面猜測下一次再見歐洲是什麼時候。
 Copyright © Jas Chen
Copyright © Jas Chen